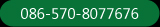洗茶煮酒问良秋
还是五月花开的时候,远在省城的姐姐托人捎来一盒西湖龙井,叮嘱我好好保存,不许转赠:这是明前茶,好不容易留下的。姐姐不是我的亲姐姐,但姐姐比我还了解我自己,更知道我急性子,压根就藏不住好东西。
姐姐国庆要来,好茶得让她见到真身。这让我犯了难。我并不好绿茶,即便偶有入手,也分分钟转手送给了珍惜它的人,对绿茶的保鲜技能也因此生疏得很。按照朋友的指导,它们进了冰箱冷藏,期间需要间隔一个漫长的盛夏,我不知道那两小罐子宝贝,该出手时品相还能不能拿得出手。
晚上无事,煮了壶普洱于窗前慢饮.随意收藏的普洱够年头了,煮出的汤色暗红透亮,嘬一口暗香满颊。电视里的工厂剧跌宕反转,错落间,儿时那些粗茶香糙饭糯的日子,恍然于忘川之上。
记忆里,最新鲜的绿茶都是装在套了塑料袋的大口袋里的。茶叶由老家的爷爷奶奶和叔叔一家人亲手种植采摘炒制,再由叔叔一肩挑来,每次两大袋,交于父母分装,三斤两斤的卖给老厂的茶友,款项再由父亲送回老家补贴家用。新炒的茶叶味道特别纯粹,茶叶送到的那几天,临近人家门户关合间都透着淡淡的茶香,大人们则会因为贪喝几杯新茶,睡得特别晚。
也许那时的西湖龙井产量已经供不应求,也许是老家的茶叶别具特色,反正叔叔担来的茶叶每次都是不够分的。两大袋新茶基本是杭州上海籍工友预定,每人分到的几斤茶叶,都会珍藏起来带回老家送人情,剩下一些碎末才会留给自己。隔壁姐姐家人口多财务紧,每年也都会预定几斤带回杭州。散茶无包装,姐姐就用黄表纸包了放进饼干盒子里,再用报纸包几小包生石灰防潮,撑到下次探家作为各种人情打点。
那些茶叶由父母三斤五斤的分给众人,每次都尽量将秤砣往里靠一点,秤杆高高的称出去,最终合账,总金额总是要赔上一些,但父母从不跟叔叔说破。剩下的碎末留给自己,也是照价买下来 。
父母泡在搪瓷杯里的茶叶末浓得要命也苦得要命,却有着浓郁的芳香,老家的粗茶让他们上瘾。盛夏时节,疯玩回家,桌上总会有一大壶淡淡的凉茶让我牛饮一杯,那是父母专门为我和弟弟泡的,加了菊花或金银花,入口先苦后甜。关于绿茶的记忆大致如此。
成人以后没有护好肠胃,基本不再碰绿茶。而老家的茶叶则在一夜间金贵了起来,不再需要父母搭帮出手。不过种茶的叔叔上了年纪,堂弟妹们都出门谋生不愿接手,茶山就转包给了别人,听说每年的鲜茶都被杭州商人收去充了龙井,难说姐姐送我的龙井就是辗转的乡情。。
第一次喝功夫茶是在厦门一家客栈,意为解渴,却被台湾客的冻顶乌龙摆道圈粉,从此对五花八门的茶叶茶具茶宠充满好奇,也因此懂得自己适合喝发酵茶。知道喝茶“是门艺术”则是近年在杭州,好友带我去的一家茶艺馆喝他存的好茶,店名记不得了,印象深刻的是厅堂正中央着白衣弹古筝的店主,那妙曼的身影和悠扬的旋律一下子就把我带入了诗情画意。
落座茶室,听一位妙龄茶艺师一样一样娓娓道来,茶史茶器茶叶洗茶泡茶闻香敬茶,令我眼花缭乱中暗自惭愧自己白白糟蹋了这么多好茶叶,差点忘了来此的目的。
据说??“茶艺”的概念最初为台湾人所出,乃“以艺衬茶,品味岩韵”,无论艺能如何,主旋律还是品茶。 而此番茶香飘飘,茶女妖娆之茶艺,可谓是一种艺术享受,也可说是一种艺能展示,也可能是潜在的产品营销,唯独少了喝茶那种于无声处荡气回肠的气场。
其实手捧闻香杯的时候,我是真的有一丝感动的,只是我不喜拘泥于繁琐,喝茶就安静的喝呗,一泡两泡七泡,七分茶水三分情,淡了倒掉换茶再来,如此而已。相比流于形式而无神韵,也许泡茶的心比泡茶的技巧更为重要。太过执著于每一个泡茶秩序,不肯放过每一个板眼,会让我觉得套路太深,觉得自己是来学艺的,然后分分钟出戏。
“俗人多泛酒,谁解助茶香”,据说这是禅茶一味的日常境。
我倒是更喜欢雅俗共赏,把拿腔捏调的茶艺变成市井。比如姐姐来的时候,我们可以先来个青梅煮酒到微醺,再来杯西湖龙井去浊气,然后再暖洋洋的打个盹,醒来后,用我的“鸟巢”咖啡机消耗几颗大杯“子弹”,不加糖,也不加奶,就这么苦巴巴的就着桂花香洗茶煮酒,毛豆湖蟹,细赏金秋。